27
方濟會-蔡俊源神父
「源」來自與主相遇
「源」來自與主相遇
@小妮/Y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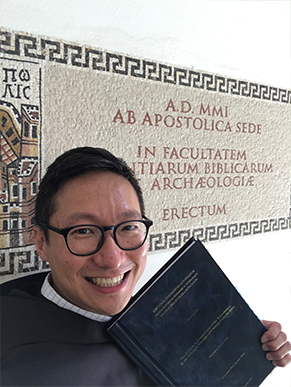
蔡神父是家中首位領洗方濟會蔡俊源神父於2021年起,在聖神修院教授聖經希臘文和對觀福音課程。這名年青神父成為方濟會士,說是一種緣份。
跟方濟會結緣
蔡神父是家中首位領洗。他回想是當年讀天主教中學時,儘管自己犯錯迷失,但宗教老師和校監仍對他不離不棄,更寬恕和原諒他,鼓勵他去聽道理。1997年升上中六後,蔡神父終決定在聖文德堂慕道,那時他是首次接觸方濟會。
到了二千年他剛大學畢業不久,正在找工作,卻感前路茫茫,有教友邀請他參加當時任堂區司鐸的夏志誠主教帶領的意大利朝聖團。「當時朝聖團還欠一、兩人便可成行,而在我被邀請的那刻,是我最感失落之時,被獲邀請有種『被需要』的感覺,便答應參加。」現在回想起來,蔡神父坦言,天主是很聰明,會觸碰到人內心深處的渴求。
朝聖團其中一站是亞西西。出發前,蔡神父幫忙搜尋有關聖方濟和方濟會的資料,期間被一張方濟會會士笑容可掬的照片所吸引。「我在想為何這班會士可以笑得那樣開心?他們是如何生活的?」他更被聖方濟的生平事蹟所吸引。「尤其聖方濟在主教府前說只認天主為父,把身上所有東西脫下還給地上的父親的這段事蹟,深深打動我,感受到聖方濟能在人前對自己的信仰表達得如此坦蕩。」由於聖人的決心,使蔡神父在朝聖時不斷問天父想他怎樣?他更向聖母祈禱,求她助佑自己能找到一份工作,以作為測試,看自己是否適合工作,抑或應度修道生活。
朝聖完後,蔡神父回港獲得工作機會,在努力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他開始辨認自己的聖召。發覺通過聖體聖事和告解聖事讓自己獲益良多,加強自己要成為司鐸的心願,決意通過這兩件聖事幫助他人。就這樣,蔡神父加入了方濟會並開始過團體生活。
度修道生活
從來修道之路總有挑戰起伏,但蔡神父慶幸當中有天主的陪伴。「初期培育時要接受一些輔導,以揭示自己跟原生家庭的關係,並與自己作修和。那時突有一個念頭,很想有自己的家庭,並把好的價值觀承傳下去。要發初願時,自覺須暫停做退省。那時在祈禱中看到聖母,她帶我到耶穌跟前,而我收到的訊息是,我做任何決定都會有基督的祝福。」
退省後,有一天蔡神父在九龍城公園散步準備離開的時候,迎面看到陽光下有對夫婦推著嬰兒車,他不期然降福他們。「我其實還未發初願的。但那時的感覺讓我發覺家庭是很美好,但降福家庭同樣是很美好,我不用執著於要有一個家,因為任何事都有天主的祝福,我更願意成為分施天主祝福的那一位。」結果蔡神父成功發了初願,繼而成為司鐸。「是天主引領我一步步走向這條路的。」
聖體聖事和告解聖事的影響
蔡神父指出,在整個被召叫、修道和神修輔導的過程,他不斷問天父:甚麼為人得著是最大?生命可否更有意義?天父想他怎樣?在探索的過程中,他領受到「天主會給我答案,用我的生命施放聖事,並學習方濟表明信仰放下一切,對於我來說是最開心、最有意義和最豐盛。」
最終能成為司鐸,蔡神父歸因於聖體聖事和告解聖事,這兩件聖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以往工作上遇到挑戰,每每參加平日彌撒,聖體聖事和福音總能觸動到我。告解聖事則讓我看到自己軟弱的一面,但更能感覺到天主沒離棄我,讓我緊跟隨著他。這是基督徒的召叫。我經常提醒自己在告解聖事中要成為天主的使者,給教友寬恕和仁愛。」
夏志誠主教是蔡神父的神師,在靈修培育上經常作出陪伴,當時蔡神父就想把這份得著傳給別人,讓別人也能受惠。「神修、告解聖事和聖體聖事讓我有更大決心揀這條路。」
聖地讀書不一樣的經歷
初進方濟會,蔡神父的主要工作是做方濟靈修和堂區工作,從沒想過要教書,但天主的安排往往很奇妙。「當年讀完神哲學要再進修,我想往羅馬讀基督論,再進修方濟靈修。但修會說思高聖經學會缺人,又是天主的召叫和被需要,我便往聖地讀書。」
蔡神父坦言初到聖地讀書有很多不適應,加上爸爸病重,對他造成一定的影響,甚至懷疑自己患上抑鬱症。
「當時覺得天主要我往聖地讀書,是把我從家庭、修會和香港抽離出去。但現在回想起來,是天主對我信心的一種考驗;看我面對這些最切身的問題時,有沒有全心全意交託給祂。天主教曉我:祂要我做一件事,我就要把這件事做好,不要有其他的顧慮;祂亦教曉我要投靠聖母。而在我的學習上不多不少都有聖母在。」
蔡神父在聖地讀書時,無論學習有多忙,每晚都會上住處的天台,向遠處的一尊很大的聖母像誦唸玫瑰經,把一切交託給聖母。他亦培養自己每天祈禱,並把三個意向—家人、修會和自身聖召—交託給天父。
在聖地讀書第二年,蔡神父的父親病情突然惡化,修會讓蔡神父回港作陪伴,兩、三周後他父親安詳回到天家。
主奇妙的安排
「在父親離世的過程中,看到天主的陪伴和愛,亦相信父親願意成就今天的我。」蔡神父提到因父親的病,他能每年回港探望他一次。「但每次要回聖地都很辛苦。爸爸卻從沒有叫我留下來,若他要我留下來,我很軟弱,我會向修會說不再讀書。但爸爸從沒這樣說,我想他亦想讓我繼續。」
當年蔡神父領洗的最大心願,就是父母也能領洗,他一直為此作祈禱。直至十七年後,父母終肯首領洗。而最美的是,幫他們領洗的就是已成為司鐸的兒子—蔡神父。「任何事天主都有祂的時間表,若當年我領洗後爸媽隨即領洗的話,就不會是我幫他領洗了。他們把肉身的生命交給我,我把靈性的新生命給他們,這神聖的交換很美,我從沒有想過會這樣。」
完成父親的逾越聖祭後,蔡神父豁然開朗,全心投入學業,更愛上研究聖經,甚至經常在聖地帶朝聖團。
畢業後蔡神父回港順理成章地開始在聖神修院教書,並負責推動聖言的工作,如在堂區和學校等開辦講座、為思高聖經學會工作,以及幫修會帶意大利和聖地的朝聖團。
曾在聖神修院讀書,現又在修院教學,蔡神父最開心是可以再度團體生活。「無論是團體日,或跟同學一起讀書,或在茶水間聊天,都是很開心的事,跟在國外和聖地讀書的風氣很不一樣。」
不過,蔡神父坦言,至今仍未習慣「教授」這身份。「教授的形象一般都是較為嚴肅,我卻不是這樣。我的修會強調謙虛小兄弟,故不想被視為教授的身份來跟大家上堂。我反而覺得聖經是很生活化,堂上會跟同學分享聖經和很多我個人的生命分享。我現在仍在摸索自己的身份,但覺得現時的狀況也很舒服。」
每日的靈修秘訣—Me Time
作為司鐸每天的工作都很繁重,加上還要兼顧教學,蔡神父笑指,自己肉身上的「充電」,就是爭取時間睡覺;至於精神上的「充電」,就是給自己一個「Me Time」。
「即使主日,早上主持彌撒、下午辦講座,我中午都會抽一個很短的時間,回到修會自己的房間,或一處安靜的地方如公園,靜靜坐下來十至二十分鐘;又或到修院的天台走一圈。這是一個靜下來、甚麼都不做的時間,讓自己可以充電。我是內向的人,需要這樣的一個時間,它不用太長但是必需。」蔡神父形容,「Me Time」就像路加福音中描述耶穌獨自上山向天父祈禱。「我需要一些時間,不管長或短,獨自上山祈禱。」
聖母的眼神
訪問中發覺蔡神父跟聖母的關係非常親密,請他談跟聖母的關係。「相對於一些教友,我不算非常熱心。我只是領洗後不久有個習慣,在完了彌撒後會到聖母像前跟她祈禱。」
「進修會後發現有一張痛苦聖母的相片:聖母聖心有七把利劍插著但眼神卻很溫柔。我覺得她的眼神很像蒙羅麗莎;你如何看著她,她都像在回望著你。這讓我覺得很親密,我會望著她的眼神來祈禱。」
「後來在修會的祈禱經驗中,聖母帶我走到耶穌面前,像保護著我一樣。這份被保護、被帶領的感覺讓我感到很安心、很舒服。故遇到大問題時,我就求聖母,望著那痛苦聖母的相片,為我的意向向聖母祈禱。」
後記
作為年青神父,蔡神父亦想多接觸年青人。疫情期間,他雖有開直播,亦有辦講座,但參加多不是年青人,他仍在摸索跟年青人接觸的方法。「可能從社交媒體著手,因為青年人都在那裡。互聯網跟現實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年青人都不會(從互聯網的世界)走出來,我們反要進去接觸和牧養他們。」